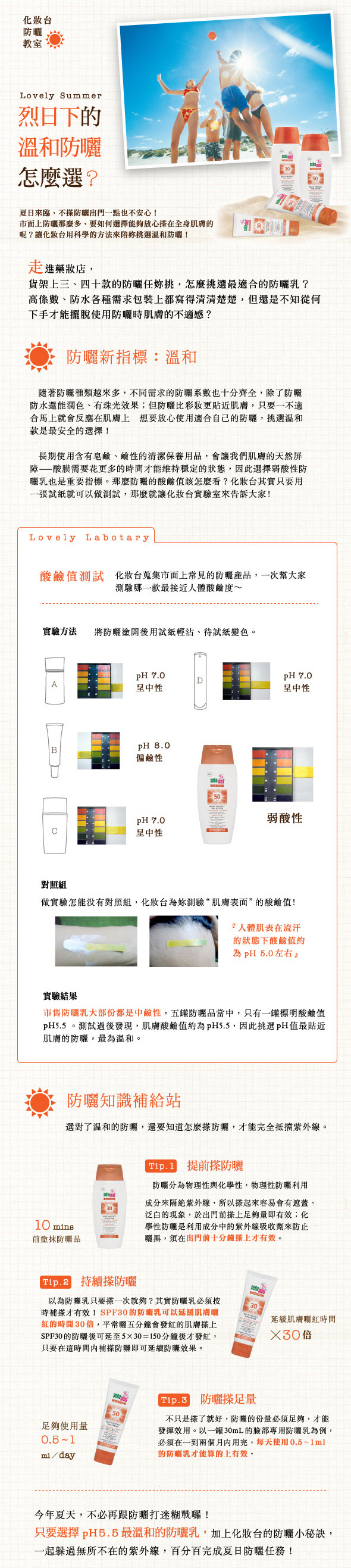http://channel.pixnet.net/reading/event/info/1312
生命中最悲慘的遭遇,
真有可能完全自記憶中根除?
如果在根除記憶的過程中出了差錯,
人生又會如何變化?

十一月的深夜裡,在暗無人煙的森林裡,馬克‧魯卡斯獨自來到一棟木屋前,遲疑許久,然後用那隻骨折的手唯一還完好的一根指頭,按下了門鈴。
他沒有聽見門鈴聲,屋子裡沒有任何光線、聲響、動靜,顯示有人將來應門,儘管如此,當門突然開啟,像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打開,馬克卻絲毫不覺得納悶。
應門的精神科醫生身穿西裝,領帶打得中規中矩,彷彿他一向在夜裡看診。
馬克費力央求著,「你得要告訴我,我不知道我出了什麼事……」
於是,在醫生的協助下,馬克開始回憶這些日子以來所發生的一切……
※ ※ ※
馬克現年三十二歲,是個法學博士,從事輔導街童工作,十七歲便和珊德拉相戀,進而結婚。但在六個星期前,懷有身孕的珊德拉在一場車禍中身亡,駕車的馬克雖然倖存,卻失去了對車禍前幾個小時的記憶。岳父說他後頸部位有一碎片插入,若不善加醫治,可能導致脊椎麻痺,因此他定期回醫院更換繃帶,並服用藥物。
車禍的夢魘揮之不去,馬克依稀想起在車禍發生前,他曾和珊德拉為了某事爭論,但始終想不起最關鍵的部分。他深受回憶折磨,有一天,在候診室裡翻閱一本雜誌,無意間發現一家名叫布萊伊托的心理醫院所刊登的廣告,標題是「學習遺忘」,該醫院聲稱正在研究一種能讓人遺忘痛苦回憶的方法,徵求自願者參與實驗。一時衝動之下,馬克便以email回覆表示願意參加。
一天,馬克成功地勸阻了一名企圖自殺的少女,正要離開現場時,布萊伊托醫院的院長說服馬克和他一起到了醫院,此時馬克已然改變心意,不想再參與該實驗,但仍虛應故事,接受了一些初步的檢查。
離開醫院後,馬克發現自己的人生大亂。他回到住處,發現鑰匙不合,更駭人的是,門旁的名牌上赫然寫著他太太娘家的姓氏「希納」,他惶惑之餘用力踢門,結果竟有人來應門,更不可思議的是,應門者居然是珊德拉,而且一副完全不認識他的表情,又迅速把門關上。
馬克覺得自己瀕臨瘋狂,由於吃藥的時間到了,而他進不了家門,拿不到藥物,便想去拿車裡的備份藥物,卻發現他的車不翼而飛。他想打電話給岳父,卻發現手機裡的電話簿一片空白,他請計程車司機試著撥他的手機號碼,結果他手中的手機未響,另一端卻有人接起了電話,並聲稱他便是馬克‧魯卡斯,那人身後並響起了珊德拉的笑聲……
死去的人突然復活;幾棟大樓在轉瞬間憑空消失;被關在自宅地下室的人拿書給自己看,在書裡,可以讀到幾秒鐘後將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這一次的背後,究竟藏著什麼?

瑟巴斯提昂.費策克(Sebastian Fitzek)
一九七一年生於德國柏林,唸過半學期的獸醫系,之後轉攻讀法律,通過第一次國家考試,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專攻著作權法。求學期間曾在柏林電臺實習,參與眾多廣播與電視節目的製作,目前仍活躍於此工作領域。
在懂得如何寫請假單的那一刻起,他便發現了自己的寫作才華。
隨處可寫作,看他剛好人在哪裡,也看筆記型電腦跟他到了哪裡。創作第一本小說《治療》期間,在家中的每個地方都寫過(沙發、床舖、書桌、浴室……),有時也在搭火車的途中,甚至是旅館的大廳裡,仍是寫作不輟。不需要特別的環境,一旦開始寫就自然而然地融入書中人物的世界。隨著作品的增加,目前習慣在窗邊的書桌工作,窗外的景色愈宜人,小說的情節愈緊張刺激。

馬克‧魯卡斯在猶豫。他把骨折的手唯一還完好的一根指頭擱在那個老舊門鈴的黃銅按鈕上,好一會兒之後才提起勁來按了下去。
他不知道現在幾點了,這幾個鐘頭以來他所受到的驚嚇也剝奪了他的時間感。不過,在這遠離塵囂的森林裡,時間似乎本來就沒有意義。
十一月的冷冽寒風和下了幾個小時的雨雪稍微小了下來,就連月亮都暫時從散開的雲層後面發出朦朧的光,在這個又冷又黑的夜裡,月亮是唯一的光源。沒有跡象顯示這棟爬滿長春藤的兩層樓木屋裡住著人,就連屋頂尖端那座嫌大的煙囪看來也並未使用。馬克也不曾聞到壁爐中燃燒的柴火所發出的特有香氣,今天上午在醫生家裡把馬克喚醒的就是那股香氣──那是在十一點多,他們第一次帶他到森林裡來見這位教授的時候。當時他就覺得自己病了,病得命在旦夕,然而,在那之後他的情況更是急遽惡化。
就在幾個鐘頭之前,從他的外表還幾乎看不出衰敗的現象。此刻血從他的嘴巴和鼻子流出來,滴在他髒兮兮的運動鞋上,碎裂的肋骨在他呼吸時互相摩擦,而他的右臂軟軟地垂在體側,像個螺絲沒上緊的零件。
馬克‧魯卡斯再次按下那個黃銅按鈕,還是沒有聽見叮咚、叮噹或是嗡嗡的鈴聲響起。他往後退了一步,抬頭望向陽台。陽台後面是臥室,白天裡從那兒可以看見屋後那座小小的林中湖泊,美的令人屏息。在無風的時候,湖面宛如一塊窗玻璃,色暗而光滑的一片,假如有人扔進一塊石頭,就會裂成千百個碎片。
臥室裡還是一片漆黑,就連那隻狗也沒有叫,馬克忘了牠的名字。他也沒有聽見當屋中人半夜從睡夢中被吵醒時,通常會從屋裡傳出的各種聲響,沒有人打著赤腳跑下樓梯,沒有人穿著室內拖鞋踢踢咑咑地走在地板上,拖鞋的主人也沒有緊張地輕聲咳嗽,試著用一點口水把散亂的頭髮撫平。
儘管如此,當門突然開啟,像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給打開了,馬克絲毫不覺得納悶。這幾天以來他碰到了太多無法解釋的事,乃至於他沒花半點腦筋去想這位精神科醫生怎麼會服裝整齊地站在他面前,身穿西裝,領帶打得中規中矩的,彷彿他一向是在夜裡看診。說不定他是在這棟曲曲彎彎的小屋的後半部工作,研讀舊的病歷資料或是哪一本厚書,屋裡到處散放著探討神經心理學、精神分裂、洗腦以及多重人格的書籍,雖然這許多年以來,他的工作只限於以專家的身份提出鑑定報告。
馬克也沒有多想,為什麼從放置壁爐的房間裡露出來的亮光直到此刻才透到外面來。那道光線被櫃子上方的鏡子反射出來,有一瞬間教授的頭上彷彿頂著光環。接著那位老人向後退了一步,而那圈光環就消失了。
馬克嘆了口氣,筋疲力盡地用沒受傷的那個肩膀倚著門框,舉起那隻骨折的手。
「拜託……」,他央求著:「你得要告訴我。」
說話時他的舌頭碰到鬆動的門牙,他咳了起來,一小滴血從他鼻子裡落下來。
「我不知道我出了什麼事。」
醫生緩緩地點點頭,彷彿要移動頭部對他來說很困難。換做是其他任何人,看到馬克這副模樣都會嚇一跳,可能會害怕地把門關上,不然至少會馬上去叫救護車。然而尼可拉斯‧哈博蘭德教授沒有這麼做,他只是站到一旁,用憂鬱的口吻輕聲地說:「很抱歉,可是你來得太晚了。我幫不上你的忙了。」
馬克點點頭,這個回答在他預料之中,而他也已經做好了準備。
「恐怕你別無選擇!」他說,從他那件破爛的皮夾克裡掏出了槍。
**
教授走在前面,沿著走道往客廳走。馬克緊跟在後面,手槍始終抵住哈博蘭德的上半身。他很慶幸老人沒有轉身,不至於察覺他虛弱得隨時會暈厥。馬克才踏進屋裡,就覺得頭暈。所有那些在這幾個小時裡讓他所受到的心理折磨更加難熬的症狀:頭痛、想吐、冷汗直流……頓時全都再度出現。此刻他巴不得抓住哈博蘭德的肩膀,讓自己被拖著走。他疲憊不堪,而那條走道似乎比他第一次來訪時更長,幾乎沒有盡頭。
「聽我說,我很抱歉。」他們走進客廳時,哈博蘭德又說了一次。那個客廳最顯眼的特徵就是一座開放式的壁爐,逐漸微弱的爐火在裡面緩緩燒盡。教授的聲音聽起來很平靜,幾乎帶著同情。「我真的但願你來得早一點,現在時間不太夠了。」
哈博蘭德的眼神不帶一絲表情。如果他心裡害怕,那麼他遮掩得很好,就跟那條老狗一樣。那狗睡在窗前的一個小籐籃裡,他們走進來的時候,那團土黃色的毛皮連頭都沒有抬起來。
馬克走到客廳中央,拿不定主意地環顧四周。「時間不太夠了?這是什麼意思?」
「看看你自己吧,你的情況比我的屋子還糟。」
馬克也對哈博蘭德報以微笑,就連這樣他都覺得疼。的確,這屋子的內部裝潢就跟屋子座落在森林中一樣不尋常。沒有一件家具跟其他的家具相稱,一個堆了太多東西的IKEA架子跟一個畢德麥爾時期的典雅櫃子並立,整片地板上幾乎都鋪著地毯,其中一塊一眼就看得出來是浴室用的踏墊,顏色也跟那塊手織的中國絲質地毯不協調。這不禁讓人想起一個雜物間,然而在這些擺設之中似乎沒有一樣是偶然的,每一件東西都像是過去留下來的紀念品,從放茶具的推車上那具留聲機到那張皮沙發,從那張高背單人沙發到那些麻質的窗簾。彷彿那位教授害怕若是扔掉一件家具,就會失去生命中一個重要階段的回憶。那些醫學專業書籍和雜誌不僅放在書架和書桌上,也堆在窗台和地板上,就連壁爐旁邊的柴籃裡都有,像是讓所有的雜物產生了關連。
「坐下來吧。」哈博蘭德請他坐下,彷彿馬克依舊是個受歡迎的客人。就像今天上午,當他們把不省人事的他放在那張舒適的軟墊沙發上,那些靠墊讓人有在其中淹沒的危險。不過,此刻他最想做的是坐在爐火前面,他覺得冷,這輩子他從未覺得這麼冷過。
「要我再添點柴火嗎?」哈博蘭德問,彷彿讀出了他的念頭。
不等他回答,哈博蘭德就走到柴籃旁邊,抽出一塊木柴,扔進了壁爐裡。火焰往上竄,馬克有一股幾乎壓抑不住的渴望,想把雙手伸進火裡,好驅逐他體內那股寒意。
「你出了什麼事?」
「嗄?」他需要一點時間來把目光從壁爐移開,再度把注意力集中在哈博蘭德身上。教授把他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
「你身上的傷?發生了什麼事?」
「是我自己弄的。」
出乎馬克意料之外,那位年邁的精神科醫生只點了點頭。「我已經料到了。」
「怎麼說?」
「因為你在自問你到底存不存在。」
這個事實似乎狠狠地把馬克按在沙發上。哈博蘭德說的沒錯,這正是他的問題。今天上午教授還只是含混地暗示,但此刻馬克想要弄個清楚,因此他才又再度坐在這張軟軟的沙發上。
「你想要知道你是不是真實的。你把自己弄傷也是出於這個原因,你想要確定你還有感覺。」
「你怎麼知道的?」
哈博蘭德把手一揮。「經驗。我自己也曾經處於相似的處境中。」
教授看著腕上的手錶。馬克不太確定,但他依稀看見錶帶周圍有好幾道疤痕,看起來不像是刀傷,而比較像是燒傷的痕跡。
「我雖然已經不再正式看診,卻並沒有因此失去我的分析能力。可以請問你此刻有什麼感覺嗎?」
「我覺得冷。」
「不覺得痛嗎?」
「痛還可以忍受。我想我受到的驚嚇太深了。」
「可是你不覺得到急診處去會比較好嗎?我這兒連阿斯匹靈都沒有。」
馬克搖搖頭。「我不想吃藥,我只想要確定。」
他把手槍放在茶几上,槍口對著依舊站在他面前的哈博蘭德。
「請向我證明我的確存在。」
教授伸手到後腦,抓了抓那頭灰髮裡髮量稀疏的部位,約有杯墊大小。「你知道談起人和動物之間的差別,一般是怎麼說的嗎?」他指著躺在籃中的狗,牠一邊睡一邊發出不安的呻吟。「差別在於自覺。我們會思索為什麼會有我們,我們什麼時候會死,還有死後會發生什麼事,而動物卻不會費半點心思去想牠到底存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哈博蘭德一邊說,一邊朝他的狗走過去。他蹲下來,慈愛地把那毛茸茸的頭捧在手裡。
「泰山甚至不會在鏡子裡認出自己來。」
馬克把一點血從眉毛上擦掉,他的目光移向窗戶,有那麼一瞬他以為看見了外面的黑暗中有一道光,但他隨即明白那只是壁爐的火光反射在玻璃上。雨想必又下大了,因為窗玻璃外面覆蓋了一層小水珠。過了一會兒,他在遠遠湖面上的漆黑中發現了自己的倒影。

【活動方式】
生命中最悲慘的遭遇,真有可能完全自記憶中根除?
如果在根除記憶的過程中出了差錯,人生又會如何變化?
請引用本篇文章並將內容試閱文轉貼到您的部落格中,在下方「我要迴響」處回覆「我想獲得《記憶碎片》新書一本!」並附上您的部落格連結網址,讓我們知道您已轉貼本書訊息,就有機會獲得《記憶碎片》 新書一本!
※請勿抄襲、複製其他使用者的回覆內容,若經小編發現或是user檢舉後確認無誤,將取消該次得獎資格。
【活動贈品】
《記憶碎片》新書乙冊,共5名。